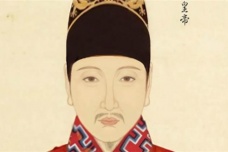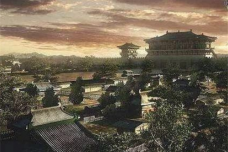吟诗颂香
「独坐闲无事,烧香赋小诗」,吟诗咏香是文人雅士品香后的风雅见证。文人的焚香活动从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全方面地体察香与周围环境所共同形成的意境,并通过自身敏感细腻的感受力将其主观地升华静坐为一种情感体验。
对于风雅的文人而言,香不仅仅散发气味,不同的香所含有的微妙气息更是有语言、有灵魂的。
宋代陈去非的《焚香》:「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即将无限意,寓此一主烟。当时戒定慧,妙供均人天。我岂不清友,于今心醒然。炉烟袅孤碧,云缕霏数千。悠然凌空去,缥缈随风还。世事有过现,熏性无变迁。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
炉中一柱香烟如云,袅袅升起,呈现碧色,又慢慢散开,一缕一缕变化成细雾上千,凌空而去,随风飘渺,在悠然的香气中安静阅读、参悟道法、消解尘缘。
品香悟道
文人雅士的用香文化是经过用香功夫的学习和涵养修持之后升华而成的一种生活诗意和美感,是一种内化后的精神提炼。
《陈氏香谱》中记载了黄庭坚收录的一款名为「意可」的香方,其中的跋文说,此香由山谷道人从东溪老处获得,而东溪老从历阳公处获得。
众生的行为力量不可度量,将此香在鼻端环绕二十五次,要想增上一定要此香才可。
况且用酒泡玄参,用茶熬煮紫檀,鼻中已充满这种香气,可持续地证悟不生不灭的诸法之相。
有心之人以鼻参此香,对佛法之理定会处处参透。以香参禅道最早见于《楞严经》,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
其中香严圆通篇中提到,香严童子闻沉水香发明无漏,通过鼻根入圆通,证得罗汉果位,获得解脱和圆通之顿悟法门。
品香悟道并不是贪恋香气,使自身失去本心,而应做到嗅香时休止:
随所闻香,即知如焰不实,若闻顺情之香,不起著心;违情之臭,不起瞠心;非违非顺之香,不生乱念,是名修止。
即当闻香之时,若利用鼻子对香气过度用力捕捉,其实是虚无没有根据的,而如若能做到内心不被香气所牵制,不因顺情的香气著迷,不因违情的香气惊恐,才能证得周围法界,到达圆通无碍的精神法门。
雅集斗香
燕居焚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文人雅士常在花园庭院或幽室之中设香席以「试香」,士人借香这种媒介相聚,寻求共同的精神追求。周嘉胄《香乘》卷十一有载,「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曰香会」,说的是雅会斗香。
品香斗香时需要有一系列规则指引,除了对香气的风格、香雾的形态、留香的时间等香料本身的品质的考评以外,对焚香的环境要求也极为考究苛刻。
从香具的形制、材质到香几、香桌的配搭、再到周围光、声、色环境的配合,力求与香品的气质相辅相成,不得产生违和之感。
因此文人雅士对香席仪规也自有一些审美规范,不同的焚香情景和状态应配以不同的香具。
明文震亨《长物志》中有说,在花园中焚香,最适合在天然形成的山石之上放置木鼎式的香炉,便更见山林野趣,有返璞归真之感。
怡情悦兴
文人雅士爱香用香,不但焚之,也常要风雅蕴藉、暗香浮动。将阴乾香草製成的香囊繫于衣袖中的肘臂上,香气自袖筒中隐隐散出,可谓袖底生香。
唐冯贽《云仙杂记·大雅之文》中有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熏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
可见,用香已被文人内化为日常的修行,更有尊敬与礼节的意味在。士人亦以香熏书,不仅可以防虫,阅读时更有缕缕暗香袭来。
古代文人也在墨中添加香料,书画时墨汁清香,提神醒脑,同时亦可为书画防虫。
「松烟二两,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许,以胶水嫂作挺,火烟上熏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皮末色碧,其色俱可爱。」是为南朝梁代冀公制墨的配方。
另宋人张遇的「油烟制墨」:「以油烟、麝香、樟脑、金箔制墨,状如钱子,因以闻名。」又有「吴叔大以桐油、胶、碎金、麝香为料,捣一万杵,而使墨光似漆,坚緻如玉,因以扬名」。
中国熏香文化数千年历史,宋元明清以来更因文人的广泛参与而绚烂多彩。
著书立作、吟诗颂香、品香参禅、雅集斗香、怡情悦性都是文人雅士参与用香的方式,对香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