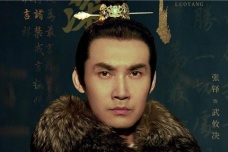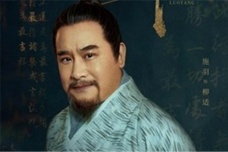在此期间,胡适受到了晚清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深的就是梁启超。后来胡适在《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评价梁启超道:“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文章,他不避讳排偶,不避长短,不避佛学名词,不避诗词典故,不避日本输入新名词。”
而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新文学之八个要点:“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正是改良自于梁启超的思想。
1906年,胡适考取中国公学后,在朋友的劝说下加入了竞业学会为白话旬报作编稿,旬报的实质是宣传革命,故而使用白话文。清末的白话报不少,但大多昙花一现,而竞业旬报竟然幸运地坚持了长达一年的时间。
正是这一年的旬报编辑给了胡适总结发表思想和训练白话文文章的机会,从此白话文成为他的一种武器和工具,并为日后他倡导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
胡适在《四十自述》写道:“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胡适出国求学,师从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
1910年胡适结束了在上海公学教学的事务,同年考取了赴美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4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他离开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杜威是美国美国实用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美国三大哲学家之一。他主张对世界的本原的认知是经验主义和认知论即是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一切知识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用以应付环境的工具,思维是工具性的,真理也是一种人造的工具。哲学要从静观转为实用,关键是把经验加以合理化即方法论化。
这种工具主义的认知论对胡适的影响很深,甚至为他打开了文学革命的大门。如果说童年的白话文阅读和上海的新思潮影响使得胡适笃定文学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但始终不得门而入。那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则使他坚定地以白话文作为撬开文学变革的唯一工具。
胡适在留学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1916年,开始试作白话诗;次年,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带到了中国,兴起了白话文运动。
胡适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是赫胥黎,一是杜威。
胡适的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有着开创的作用。
白话文运是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它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劳。毛主席评价胡适: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